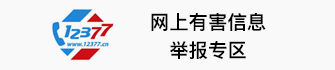比33吨井盖更沉重的,是拾荒者以及整个行业的命运。
2013年秋,河南人徐铭骏看着这片偌大的“废品”王国,百感交集。
北京五环外东小口村的土路上,开往回收厂的卡车扬起烟尘,年近五旬的徐铭骏挪着步子巡视着一个挨着一个的小院,扫视环绕四周斑驳的砖墙、变形的铁丝网,还有小山一般看似杂乱实则整齐有序的废品堆。
铜铝、塑料、纸张、木材、轮胎橡胶,广告牌上的红漆大字歪歪扭扭,划分出各自的经营范围,互不干扰。外行眼里不值一文的垃圾废物,来到这里,就分出了各自的价值。
虽然城里人对这里的脏乱差避之不及,但有人却视之为淘金圣地。
据粗略统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人员高峰时约在20万(一说30万)人左右。有的蹬三轮车走街串巷,有的租下铺面成为坐商,他们中70%来自河南,其中95%又来自固始,也就是近期哄抢33吨井盖的新闻发生地。
90年代起,徐铭骏就来到北京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到了2003年,他和几个河南老乡凑了几百万,租下北京五环外的900亩荒地,从推掉一人高的杂草灌木开始,建起1000多个简陋小院,出租给老乡们,挖到了第一桶金。
十年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散落在京城各处的河南籍废品回收业者纷纷搬来,走街串巷的拾荒者把废品运到这里。
慢慢地,东小口发展成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全盛时期有三万多人在此谋生,承载了北京四分之一的废品分类回收,年交易额高达十亿,成为有名的“废品村”。
不少早年从事钢铁等高价值废品的人发家致富了,但更多跟风而来的老乡们仅仅只能做到混口饭吃。
2012年,靠种地在固始老家已经很难维持生计,北漂多年的乔春雷就把父母也接到了东小口村堆满塑料废品、充满腐败气息的小院里。
作为行业的后来者,乔春雷没能像徐铭骏一样赶上好时候。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处于产业链底层的废品回收行业遭遇重大打击,至今也未能恢复危机前的行情。最差的时候,整整半个月,乔春雷才能收齐一车塑料发出去,而利润只有一千元。
女儿玩着废旧的玩具慢慢长大,总是感染莫名其妙的皮肤病,父母身体的病痛在常年分拣垃圾的劳作中不断恶化,还舍不得吃药。
为了增加收入,乔春雷不得不咬紧牙关借钱买车跑货运,但一场更大的行业冲击已经到来。
2014年,随着北京城区的不断延展,东小口村也从荒凉的郊区成为了规划中的商业用地,市场围墙高价回收废品的小广告边,出现了大大的“拆”字。
乔春雷咬牙决定带着家人再次向外环迁徙,但还有很多四五十岁的拾荒者只能离开北京去外地闯荡或者干脆回老家。
“干我们这行,就是不稳定。”
作为“废品村”市场管理者的徐铭骏想得更远,他把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徐源鸿喊了回来。父子俩动员起部分老乡,希望能再找一片空地,引进国外封闭式环保产业园的概念,试图进行一场行业自救。
但不论是迁徙或者回乡,这种产业清理淘汰的局面在多年之前就已有征兆。
2
“我全包下!”
当乔保锋把仅有的两千元现金拍到昌平水泥厂门卫办公桌上时,估计他自己也没料到,“破烂王”的称号会在十八年后伴随他走进铁窗。
1985年,北京到处是工地,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一个人、一辆平板车,15岁的固始少年乔保锋在满大街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商机,一个多月就赚了2000元。经人偶然指点,他又把昌平水泥厂的废旧包装袋运往山东的爆竹厂,赚了整整一万元。
1986年,乔保锋用这1万元起家,各处打点,垄断了周边厂矿的废品。十几年间,他用来存放废品的场地从几分地扩展到十几亩,还有汽车20多辆、手下50多人,昌平“破烂王”的称号从此传开,吸引了更多同乡前往北京“淘金”。
但真正让乔保锋成为传说的,是后来一连串荒诞行径。
最花边——同时娶了三个“妻子”,并且全部伪造了公章和结婚证,然后又暗地伪造三本离婚证,还自以为天衣无缝。
最无知——出资承包了一个铸造厂,为了炼钢,把井盖、自行车,下水管道统统扔到了炼钢炉里,直到一颗旧炸弹被引爆。
最大胆——在铸造厂经营失利后,非但不反思自己不懂技术,还公然偷电非法牟利。因此,昌平供电局把乔保锋厂子的电给停了。他的反应却是带着一帮人冲进供电局办公室,拿着铁锹威胁要活埋了局长。
2002年,乔保锋因伪造公章、重婚、盗窃锒铛入狱,被判有期徒刑19年。
文化低、不懂法、草莽气息重的乔保锋可以说是拾荒者大军中极端却又鲜明的写照。
在北京,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拾荒者各自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帮派”,或垄断一块城区,或占领一项细分行业。帮派之间区域划分森严,为了彼此利益冲突不断,成为了弱肉强食的江湖。
1997年,有关部门向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王维平透露,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
“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教授说,“那时,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
为了平息各个地方帮派对废品资源的争夺,王维平出面促成了十多个帮派的面对面会谈,达成了一份协议:
“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四环外接应废品回收,“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并没有改变江湖的本质,各帮派内部潜规则盛行。
比如,井盖属于公共设施,不能随意回收销赃,因而无论是谁偷的,最后都会与掌握废品收购的河南固始人联系到了一起,“河南人与井盖”的江湖传说也就从北京传播到了全国。
长期缺乏行业规范、产业升级,加之从业群体本身素质的原因,拾荒者们一直没有摆脱草莽状态,废品村更是成为各类安全隐患的重灾区。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拾荒者们最终都被打上“低端产业”的标签,面临清退的命运。
3
80年代初,当河南固始人北上“淘金”的时候,湖南新化的农民也开始背起帆布小包,走上了流动维修打字机的道路。
与乔保锋一样,新化人也是在偶然间发现了这个产业蓝海。
1960年,易代兴兄弟在家吃不饱饭,宁可被骂“不务正业”也要出去跑江湖,从事没太多技术含量的简单维修。
一次,在两人为银行修理钢板时,旁边办公桌上的打字机出现了故障。凭直觉,他们认为是一个小零件位置不对,于是就借口需要喝水,支开银行员工试了一下,以应证想法。在银行员工回来后,易代兴毛遂自荐,装了下样子,把一个零件移个位,修好了机器。
有了第一次经验,易代兴兄弟开始辗转各地,用单位里的坏打字机练手,来回拆装,边试、边修,修好了就拿钱,修不好就跑,最终掌握了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
从此,兄弟俩怀揣假介绍信和证件,以对外技术支援的名义走遍大江南北,出入各类机关单位修打字机,赚的钱让老家人咂舌的同时也吃了不少牢饭,还带出了最早一批徒弟。
1979年政策松动,新化县把这些外出漂流的人集合起来搞起了打字机维修厂,负责提供合法身份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考核。从易氏两兄弟开始,亲戚带亲戚、朋友教朋友,新化的打字机修理队伍在1990年发展到了5000多人,组建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流动维修大军。
此时,办公设备越来越复杂、先进,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也开始在中国普及,散布全国各地的新化人通过不同方式先后学会了修复印机,然后在这个以乡土关系凝聚的团体里,新的技术如原子弹链式反应一样扩散开来。
每一次新技术的引入,都带来新的商机,也吸引了更多新化人加入队伍。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了。修得多了,新化人干脆收下那些不要的二手复印机在各地开起了复印店,而后又有人从台湾人手里把进口日本废旧复印设备的生意接了过来。
从西藏到广东,从海南到东北,有了充足而又廉价的设备供应,大大小小新化复印店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个角落。
任何一个城市的高校周边,几乎都有这些抄着浓重口音的新化人开的复印店、文印店,而他们背后是“国际贸易+设备制造+专业市场+专业店”的一整条产业链,从业人口高达二十多万,涉及到全县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为了地区经济中非常典型的“新化现象”。
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一些从事外贸与零配件销售的新化人干脆在珠海、深圳等地开始了办工设备制造,一步步竟然从组装走上了自主研发。如今,新化人甚至响应起了“一带一路”的号召,把复印机出口到了非洲。
比起同样背井离乡的固始人,新化人的努力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演绎了一部励志的产业升级史。
4
新化和固始,两个都是各自省份人口最多的县级区域,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下,两地人民不约而同背井离乡,在世人嫌弃的眼光中谋求一份温饱。
虽然双方选择的行业不同,但最初都是从灰色地带找到生存的土壤,其中一度有不乏耍手段甚至败坏行业道德的事情发生,比如偷换复印机零件、撬偷井盖等。
但因为产业环境的不同,复印店与废品回收,一个脱胎换骨成为了地区骄傲的支柱产业,一个则无论从业者如何辛苦,最终都难免演变成了连累地方声誉的污点。
比起不断学习技术、不断升级的新化复印机行业,北京的废品村里除了像徐铭骏那样从内部自发进行市场规范之外,动荡的行情、从业者低素质以及壁垒森严的江湖色彩,都让外部投资者望而却步,导致整个废品回收产业难以升级甚至还会倒退。
一旦废品回收市场被拆,拾荒者们再次退回零散的游击队模式,生存更为艰难,乱象势必丛生。
因此,所谓“河南人偷井盖”的荒诞现实背后,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讲是一个产业的困境。
即便问题重重,十几万拾荒者却是北京城市生态循环必不可少的环节。据王维平统计,他们不仅帮助政府节省每年数亿元的垃圾处理费,还用精细的人工分拣,使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回收利用。
据环保NGO“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估计,可回收资源往往能占到垃圾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近90%都得到回收。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
这里的一大功劳,要归于由拾荒者和商贩组成的、庞大而高效的“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
然而随着一轮轮产业整顿,在一次次漂泊迁徙中,北京废品回收从业人口已经下降到十万左右。与此同时,北京市的垃圾却以每年8%~10%的速度快速增长,垃圾处理和废品回收的压力越来越严峻。
但未来的曙光已经出现。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全国推广势在必行,垃圾分类产业终于迎来了大变局。短短一个月就有1004家垃圾分类企业成立,投资者闻风而动。
在北京,子承父业的徐源鸿于2017年创办的互联网垃圾分类公司也迎来了多家投资机构。
作为在北京的河南第二代废品回收从业者,徐源鸿见证了这个小时候羞于对同学提及的行业变成今天资本争相追捧的风口。
“如果徐总找着了地方,我还跟他一块走!”
或许徐源鸿还能记得,五年前,面对废品村拆迁危机时,河南老乡们对他父亲的这番期许。
本文来源:华商韬略
评论
全部评论(1509)
-

最新最热
行业资讯 -

订阅栏目
效率阅读 -

音频新闻
通勤最爱